
第19个「世界社工日」的清晨,与往日有着些许不同。从一通社工小伙伴打来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电话,到不断接收来自各大公益机构、网络媒体发布的关于「世界社工日」的宣传图文,欣慰与酸涩在心中相互交织。
欣慰所有社工伙伴们的故事终于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酸涩电话中原本定好要去探访临终患儿的小伙伴们,因为家属对社工职业认识的临时变化,取消了这次探访,只能带着准备好的工作包在清晨7点的车站相视苦笑。
或许这就是甘肃医务社工的真实处境,我们与医护同在医院长廊穿梭,却总在患者家属疑惑的眼神中反复解释职业职能与专业性。
感慨之余,随即问起几位全职医务社工,「为什么?」,「为什么你选择成为一名医务社工?」。
于是,我们发现答案从不在宏大的叙事里。褪去「助人者」的光环,在她们的话语中我们听到了最朴实的回答,也洞见了人类对职业本身最初的理解是真实需求,而非对专业名词的盲目认同。
尤其在开始之前,大家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我们都不是医务社工,但对医务社工有着同样的理解和共鸣。
以下内容分享给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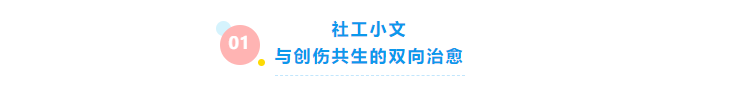
我从小患一定的眼部疾病,在上学期间经常就会有一些不好的绰号伴随着我,导致我在和别人交谈的过程中不敢与他人对视,自卑心也一直伴随着我。
直到前段时间了解到可以做手术,不过虽然做了手术但是眼部功能也有可能无法恢复,有复发的几率。从事工作后,有一个想法常常在我心中出现,如果我小时候有一名医务社工出现,可能疾病治疗会更加及时,自卑心也不如现在这般严重。
这个想法不是凭空冒出,是在我工作过程中一步步实践的结果。工作前期,我本来以为社工只用在医院里陪着小朋友玩,但真正进入医院时,一些小小的“偏见”逐个被打破。
随着时间的积累,小朋友们越来越信赖我,把我当成他们的好朋友。但是也难免遇到小朋友闹脾气的时候:“姐姐我不想和她玩,不要让她进来图书角!”、“那个玩具是我的,我想要玩,不给你玩!”。
因为治疗的原因,大多数小朋友们都被迫休学住院治疗,在礼貌方面、情绪管理方面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还有小朋友因为父母比较忙碌,由奶奶照顾,格外缺乏安全感会非常依赖我,不愿意我和别的小朋友说话,害怕我不理她。
但面对小朋友们出现的问题,仅靠陪玩是解决不了的,这时候社工的专业工作手法与超乎常人敏锐的观察力和同理心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和医护、家长建立亲密的信任关系,他们愿意信任社工,放心把孩子交给我。
于是,父母眼中孩子的问题,不再是问题,因为我知道问题背后是需求,需求背后是理解,而这份理解源于曾经让我低头自卑的伤疤,源于我想与孩子的双向疗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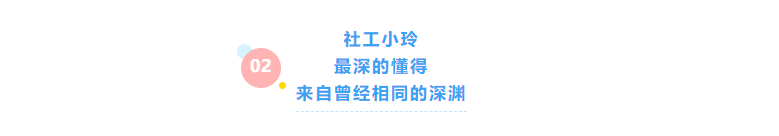
大概有两年时间,我作为一个肿瘤患者家属长时间待在医院,在那段时间里面,让我对医院生活有了更多的体会,所以,当看到彩虹医务社工招聘的第一眼,我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天选岗位。
因为我走过那段路,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与这条路上的人更多的陪伴和支持,用自己的经历给与他们希望和力量。
在医院里,希望和磨难同时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作为患者家属的我来说,我始终觉得疾病治愈是有希望的,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持过任何的怀疑态度,但是看到家人由于化疗的副反应一次次的呈现的难受状态,巨大痛苦和磨难也缠绕着我的心。
所以,作为在医院“资深”家属的我来讲,我了解他们在医院的感受,我也希望能够借助“医务社工“这个身份陪伴他们一起走过这段艰难的路程,找到希望,迎接曙光。
于是,看到眼睛红肿在我们面前故作坚强的阳阳奶奶,我马上就能「侦破」她的坚强,用时间和情感支持家庭一起走过接受孩子复发的艰难时光,给家人间创造更多表达爱的机会,因为我相信团结互助,温馨有爱是战胜一切的法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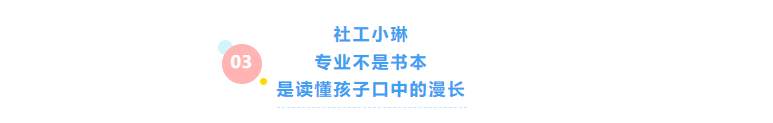
过去一段时间,我去医院的次数好像已经超过了出生后去医院所有次数的总和,但这还是远远比不上那些患儿和他们家庭在医院度过的时间的长度。
在开展病床服务的时候,最让我触动的是花花小朋友在一次绘画疗愈时对我说的话。在创作画作时,花花突然对我说她有一个问题:她觉得自己在医院的时间过的太慢了,花花虽然说得不清楚,但她说自己要治两百天才能好。
我本想鼓励她说两百天也不到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花花却说:“对你们来说一年很短,可对我来说很长。”
花花看到别的小朋友输液也会害怕地问是给她输液吗?虽然输液对她已是家常便饭,但还是很害怕。
这短短的两周,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应该更好地去理解患儿及其家庭的感受,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再一次见到花花时,她问:“姐姐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啊?”其实距离上次见到她也只过了两天而已。
医院生活让小朋友们感觉时间很漫长无趣,对于刚接触医务社工不久的我来说,一定还有很大的工作空间,但看到自己的陪伴能让病房里的他们生活多出一点点趣味,就觉得很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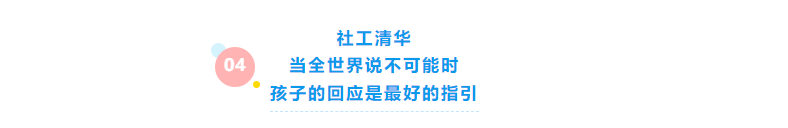
对我来说,获得一个医务社工的工作机会,经历了漫长的家庭抗争。那时,距离我考研结束已过去了快一个月,我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刷手机,我妈再也看不下去了,让我出去找工作。
临近年关,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无论如何不能再躺到家里了。参加过学校志愿服务的我打开了志愿汇,一口气报了好几个岗位,但最后收到答复的只有彩虹公益社。
第一次志愿活动是和大家一起去医院为小朋友开展小年的活动,刚走进小家(彩虹有爱儿童之家),我就被暖黄色的灯光和儿童友好的环境吸引了。
不同于我接触过或者了解过的公益组织,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想要把这件事做好,为此也在不断地和我们强调着一些注意事项,大到活动本身,小到和孩子们的沟通相处,都有非常详细地方法分享给我们。
在完成前期的准备工作后,在医院里我见到了不同于我想象那般的小朋友们。那时的他们都很有生机与活力,擅长和小朋友相处的我也很快得到了一位小朋友的信赖,她跑回病房为我拿了一个橘子,也把自己叠好的小船送给了我,这一切都让我深受感动,也让长时间倍受打击的我感到了一丝信心。
回去的路上,虽然身体疲惫,但精神却无比高涨。我突然发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和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之后,只要彩虹公益社一有活动,我就会报名参加。
在这期间我陪因大雪封路不能按时回家的小朋友一起过生日;陪在医院化疗的他们在病房里找春天。一次又一次的活动让我和小朋友逐渐熟络,也开始期待再见到他们。
那时候我也逐渐认识了更多彩虹的小伙伴,她们是同事也是朋友的感觉也让我心向往之,讨厌复杂人际关系的我更多了一个想要加入的理由。只是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是骨感的,当我提出想在彩虹工作时,遭到了家里人前所未有的阻挠。
家里人无一不觉得,你是不是被洗脑了,你当时选的专业就不做了吗?你现在说你不喜欢原专业,你早干嘛去了?长辈们普遍不了解公益行业,也不愿去了解,只固守在自己的思维里面,就算去了解,帮助打听情况的人对此也充满了偏见,觉得这是有钱人才做的事情,觉得你献爱心、做志愿者不行吗?
于是家里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一时间找工作都成了一个禁忌的话题。
在这期间,彩虹的小伙伴做起了我的树洞,她们充分地理解和共情我现在的困境,也积极地帮我想办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成了我情感上的寄托,我想如果不是她们的开解,这些事情不知道会把我逼到什么地步。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对于考公考编越来越感到绝望,也越来越敷衍,在一次家庭争吵中我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现在考上了我就是给你们一个交代,我不会做太久的,考上的那一刻我就会想着怎么出来的。”
听到这些,我妈妈崩溃了,等情绪平复之后,她开始说服自己接受这件事情。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上,一位阿姨忍不住帮她宽心:“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已经不是我们能跟得上的了,交给他们年轻人吧。”
妈妈一边听着,一边若有所思,终于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她松口了,我们长达三个多月的抗争结束了,而我的人生也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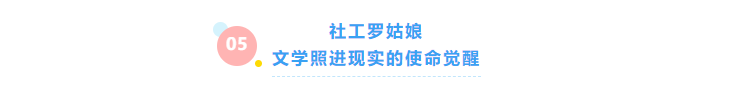
从前上学的时候,喜欢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懵懂中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生命教育。
那是第一次感觉到生命赋予给每个人的使命感,也是这种使命感让我们选择成为不一样的人,走不一样的路。
看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时,对十几岁的我还是很震撼的。而我也借由史铁生对待生命的态度,感受到身体的残缺或病痛,无法剥夺生命的尊严与可能性。
史铁生在用写作构建生命的意义,而我也在用我自己的选择构建我自己生命的意义。当然,成为医务社工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还是十分遥远的。只是说在十年前选择职业时,带着热情真诚和懵懂天真进入了公益行业,成为一名为有需要的孩子们服务的公益人。
成为一名医务社工的契机,还是遇到了一名彩虹陪伴成长助学支持的孩子,确诊白血病在兰州治疗期间,向我们发起了求助。当时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吃饭和住宿都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也就是帮助这个孩子开始,彩虹开始从提供住宿餐食支持开始,逐渐拓宽了服务领域。
从2020年5月到现在,我已经走过了6年的时光,忙忙碌碌地经历了很多事情,直到「为什么成为医务社工?」这个问题出现时,让我停下来开始思考这一路的感受。
突然发现,就像史铁生是地坛四季变化的见证者一样,我们也是异地就医重症儿童家庭的见证者,帮助家庭重建安全感,翻译医学语言,把复杂的治疗方案变成家庭可以理解的生活用语。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鼓励生病孩子的父亲利用闲散时间兼职挣取生活费,让无力照顾远方家乡的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接上来,在彩虹有爱儿童之家一起住宿,或是去到去世孩子的老家去送别孩子。
这些也让我感受到,疾病会让家庭停摆,让家庭系统中的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都突然发生改变。医务社工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家庭续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修复被疾病打断的生命叙事。
而今年,当我和小伙伴一起进入医院科室扎根服务,我突然感觉到人生的那一片拼图好像拼满了,从「为什么是我」到「我可以如何存在」,从公益人到社工到成为医务社工,补上这一片医学的人文拼图也成为了我存在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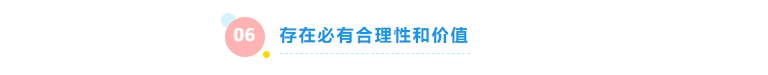
除了患儿自身的情感需求,在整个治疗期间,医患信息差、隐性医疗成本、西北地区特有的文化敏感性,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医患纠纷的导火索;
这也让我们发现,这些可见的个体需求背后,隐藏的是医疗服务框架内缺失的那一块人文拼图。
是当医疗系统用生命体征数据丈量生命价值时,社工在「被打叉」处重建起生命意义的坐标轴,用心、用力去证明:带着裂痕的生命依然具有完整的意义和权重。

此刻,窗外黄河正载着希望奔向春天。在西北有限的医疗资源中,我们作为像骆驼般扎根在这里的医务社工,一定会有机会见证更多令人欣慰的变迁。
因为一年前「医务社工」只是像名词解释一般出现在医院科室,而一年后,医务社工已与医护协同查房,共同探索多学科团队协作下的医疗新模式,未来,这样的时刻一定还会有更多!
文末,我们也想邀请您在文章留言处写下您与「医务社工」相关的故事,或是您对这一职业的理解 / 误解,或是您曾接受过的医务社工服务,亦或是您身边的医务社工故事。
或者,您可以转发这篇文章,让更多人看见医务社工的故事。
写在最后:选择成为医务社工,不是选择一份职业,而是选择永远站在生命最脆弱的裂缝处——因为那里,光最容易照进来。
🌱期待美好发生。
—END—
图文编辑:RVCH项目组
彩虹有爱儿童之家(Rainbow House)
希望每个孩子都有甜蜜的童年和明亮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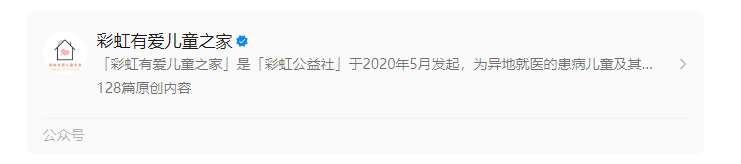
我们在这里共同努力,
为异地就医的儿童搭建「家以外的家」
有爱的家。
祝好:)善良的你
Since20200510♥

